“你有多久没有看完过一整本书了?”
在这个世界读书日,不妨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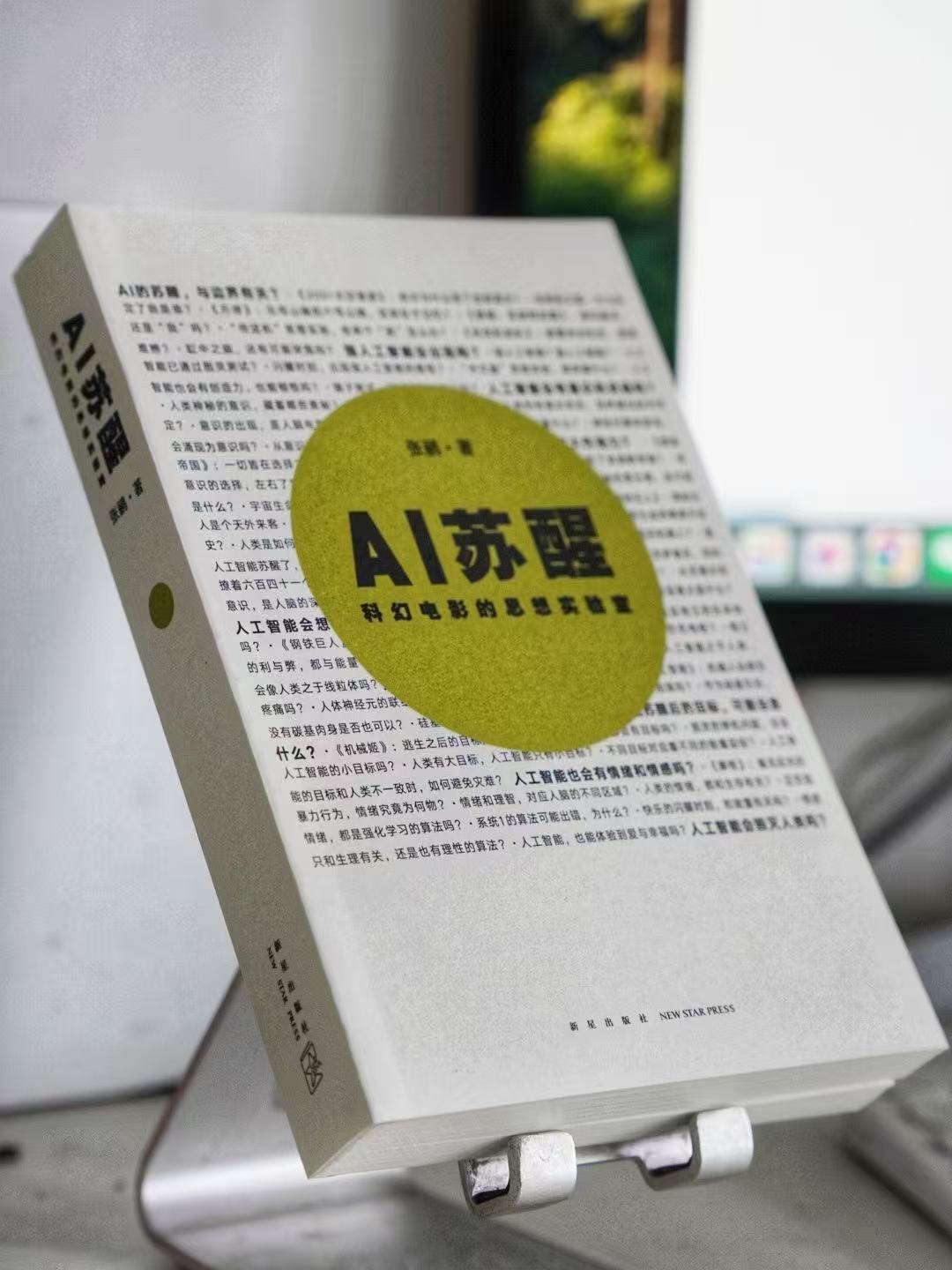
驯化
尤瓦尔·赫拉利在他那本畅销全球的《人类简史》中,有这么一段话:
“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小麦,但其实是小麦驯化了智人。……如果我们用小麦的观点来看农业革命这件事,在1万年前,小麦也不过就是许多野草当中的一种,只出现在中东一个很小的地区。但就短短1000年内,小麦突然就传遍了世界各地。生存和繁衍正是最基本的演化标准,而根据这个标准,小麦可以说是地球史上最成功的植物。……小麦的秘诀就在于操纵智人,为其所用。”
植物有辩证法的思考吗?当然没有,在更久远的时间维度之下,只不过智人也成为了小麦生存河繁衍的策略的一部分。“人与小麦”这种伺服系统在于我们生活的非常普遍,比如“灯与夜生活”、“锅与美食”,以及“阅读与思考”。
“会认字、会阅读”在我们生活的像是如同呼吸与喝水一样的一种”基础“的技能,当我们谈到读书时,很多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与大家的印象大相径庭的是,”读书习字“在五千年的历史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普通百姓无关。隋朝开设了科举制度,一只延续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一共1300年的历史,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1950到1960年代,多次扫盲运动,我们国家的文盲率才开始下降。《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的年份是1986年,扫盲与义务教育相互结合,才在21世纪之后将我们国家的文盲率降到个位数(5%以下)。
语言之中,“说”这个能力,是个人以及人类社会存在的一项基础技能,“读”与“写”只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工业革命时代之后,才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逐步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很多人感慨上学时候,语文课很难,不好学,其实这确实更加符合人的天性,所以当又一个世界读书日到来时,也无需有太多压力。不要因为达不到人均的读书数量而感到焦虑,也不需要因为没有读书而忍受那种“文化第二性”的压力。
“读书”,从来都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在久远以前的封建时代是,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生活依旧是。
媒介
四五年前,我在网上“参与”过一个很有趣的行为艺术实验,实验的内容随机挑选了20个自愿者,在一个大院子里,不携带任何电子设备,每个人相隔一米,每个人配备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笔一张纸,三个小时时间,坐在那里,不准交流对话,摄像头全程记录整个活动过程。这是一场带有点反后现代社会性质的实验,观察普通人离开了手机、手表之类的电子设备之后,会做些什么。这是一个极其无聊且黑色幽默的行为艺术实验,而更无聊的我通过互联网在平台网站上看完了整个活动过程的视频。手机在这个年代,作为一个载体,已经嵌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可能听到过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因为不知道如何使用手机上的各种软件而在生活中遭遇各种不便的事例,有没有试着尝试过完完全全丢开手机,生活三天呢?如果你读到这篇文章,真可以去试一试。
基于手机这个载体,“媒介”的变革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在过去的短短二十年间发生着惊人的变革与更替,这种从底层到表层的变化,甚至用“翻天覆体”这个形容词都难以形容。二十年前,上网的费用非常的昂贵,接入互联网需要有电脑和专门的通讯设备,在2000-2004那个年代,差不多需要3-5元/小时;二十年后呢,你会发现19/150G的流量卡,这个费用的便宜程度甚至比货币通货膨胀的速度还要更甚。在这个背后更让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生活、工作、学习等等方方面面,那些隐藏在我们角落的变化。
你有多久没使用过钱包,有多久没有使用过现金了? 你有多久没有仔细观察走过的路,而不只是遵循导航的指引了呢? 你最近一次写一段长的段落,是不是时不时卡住,忘记了某个字该如何书写?
当我们谈论起媒介的时候,必然绕不开“麦克·卢汉”和他那本《理解媒介》。媒介在如毛细血管般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辨识力,去区分开来、去追踪溯源,进而深入骨髓地去掌握每总“媒介”背后不一样的思维模式。这是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去追问“阅读”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之所在。世界读书日,我想我们更应该去追问的是,在那个通讯技术不那么发达的年代,通过“文字-纸笔”的系统,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在当下去学习和吸收,有哪些方式在当下值得去对照与反省?
王勃在滕王阁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你能从文字中感受到一种天地人的波澜与壮阔;而你在抖音上刷到的路人登上滕王阁,在手机的全景镜头的扫视中,听着背景音里一句:“我C!我C!好美啊!”,只会有神经元一个波动的毫秒级快感。从信息传递的角度上来说,一个的信息密度高度浓缩,失真但激活了你大脑之中的想象力;一个信息量极其密集,充分还原视听的所有感受,真实但刺激的是你的原始本能。两种方式,无所谓好与坏,给人带来的愉悦感亦大不同。正是因为这份不同,才有了“阅读”的意义,他提供的不仅是另一种思维的模式,也是另一种感受世界的模式。
人工智能
当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后,我听到的最为反感和不可思议的一种声音与论调是:“语言(写作)可以不用再学习了。”而现实可能恰恰相反,正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示微,以“文字-纸笔”系统为基础的“阅读-写作”能力,在人工智能的年代,会变成一种新的稀缺资源与能力。
一句自相矛盾的话是:“在文字的‘生产’便捷与廉价的年代,文字的‘产出’变得稀缺与昂贵了。”
举个例子譬如奇葩说而声名在外的罗执中,或者是“救猫与救火”一个论断而出彩的李诞,一个人的语言组织能力并不会因为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发展而被取代,反而会在这个当下具有更加强的比较优势。而这般强大的语言组织能力必然建立在浑厚而广阔的阅读的基础上的,这是读书(阅读)在当下的时代的又一层动力。
我在过去的两个月做了数场关于“人工智能”的讲座,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非常关注这项新的技术在生产效率上降本增效的方面,能够带来的改进与提升。但在这一点上,身处在这场科技变革的进行时之中,仍然非常肯定。对于语言以及文字的驾驭能力,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会得到指数级的加强,省略掉那些机械性的部分,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经历集中在创造力的部分。
积极的地方,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notebookLM或者ima,一个是谷歌的出品一个是腾讯的出品,两个引入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笔记工具,开启了阅读的“新的范式”。时代在进步与发展,身处浪潮中的人也需要不断地去学习与进步。